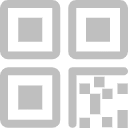龚克提出,目前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的相关应用技术、开发更加有效的算法,还需要发展一批支撑治理的技术,如监督性技术,用于保护公平性以及隐私等。比如从社会中采集的数据,其实带有一定偏见,这不是社会的错,是现实社会固有的。但如果没有适当技术对数据进行“减偏”,公平无歧视原则可能就无法落地。因此,要着力强调发展一批监管性支撑技术。 李萌认为,人工智能技术应该将普遍适用与分类推进相结合,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出差异化选择,切实保护各相关主体合法权益,提高弱势群体的适应性,努力消除数字鸿沟;同时也要尊重和帮助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替代方案,避免忽视、偏见、歧视。 邱勇提到了教育的意义,他指出,大学作为人类科技文明的重要策源地,不仅要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技术前沿努力突破创新,也要进行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,塑造良善的人工智能价值伦理。 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、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温德尔·瓦拉赫(Wendell Wallach)强调了新的国际合作方式的重要性。他认为,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具有敏捷性、适应性、预见性、响应性和包容性,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,将使其更具有可行性。同时,每个国家要处理好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双重需求之间的关系,接受国际标准的同时,积极开展旨在应对新挑战的前瞻性对话。 不过专家们也提出,人工智能治理的目的不是限制其发展,而是要为了实现向善、造福人类的健康发展。 李萌指出,目前社会对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、伦理风险和法律风险的认识,有一些是基于理性的推演预判,也有一些是基于主观判断的臆想。他认为,应该秉持积极而负责任的态度,努力实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有效规制之间的协调,技术边界拓展与应用范围限制之间的平衡,避免陷入伦理陷阱而阻碍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。
人工智能治理的目的不是限制其发展,而是要为了实现向善
关注
打赏